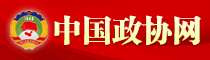- 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陈刚韦韬出席 孙大伟发表讲话
- 向着光荣与梦想昂扬奋进——热烈祝贺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 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补选十三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
- 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孙大伟出席 15位委员作大会发言
- 自治区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 孙大伟主持
- 委员分组讨论“两院”工作报告

1949年11月底,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以后,赶到广西去,参加解放全广西的战役。这天,本来想赶到兴安宿营的,但车子来不及,便在临江的一个镇子上停下来。我向老板打听这是什么地方,老板回答说:“界首。”
啊!界首!这是多么熟悉的地方呀!恰巧是在15年以前,我们曾经在这一带进行过艰苦的战斗,粉碎了敌人企图全歼我中央红军的阴谋,撕开了敌人苦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我们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告别了伤残的战友,就在这个镇子西头的渡口上,踏着用美孚油桶搭成的浮桥,跨过湘江,继续走上长征的道路。
当晚,我立即找到几位年长的老乡,谈起了当年。这些老乡们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红军战斗、渡江的情景。这时,正是刚刚进行了衡宝战役和解放桂林以后。我们一道从今天的胜利谈到过去的日子。一位老人很风趣地说:“当年反动派中央军、广西军几十万人围着你们打,也没有消灭你们;现在,你们一下子消灭了他们,打到他们老窝去了。”是的,经过长年的艰苦斗争,我们胜利了。
这一夜, 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这偶然的历史的巧合,把我又带回到了当年掩护党中央渡湘江的战场上。
1934年11月末,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以后,正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湘水兼程前进,因为敌人早已发现了我军西进的意图,利用湘江这条天然障碍,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左右有桂敌、湘敌夹击,后有五次“围攻”中的中央军主力和广东军队的尾击,企图在全州、兴安、灌阳之间一举消灭我们。情势是十分危急的,我们必须打过江去!
行至文市附近,部队经过半日休息之后,正准备继续前进,译电员走过来,递给我一封电报。电报是军团发来的,命令我们师(红三军团第五师)的十四、十五两团(十三团调归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行动,赶赴灌阳的新圩附近,阻击广西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纵队过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任务是艰巨的。就在道旁,我打开了地图,借着手电的亮光找到了阻击位置,当即向部队下达了命令:部队行进方向转向西南,以急行军向新圩前进。
下午4点多钟,我们赶到了预定的地点。显然敌人是掉队了,我们比敌人先到达了这里。派出了侦察、警戒以后,我和师政治委员钟赤兵同志、参谋长胡震同志及两个团的指挥员、政治委员来到原定阵地上。这里,离湘江有七八十里路。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正在我们面前通过,这是敌人进逼江岸的必经之路。公路两侧则是一片连绵的丘陵地带,紧紧地扼住公路的道口。时间已是深秋了,公路两侧稻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没有脱落;满山的松树和簇簇的灌木丛,约有一人深,刚好成了隐蔽部队的场所。但是这个地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这片山岭上守住,否则,过去背后的新圩直到江岸,就是一片大平川,无险可守了。我们把部队布置一下:十五团在左翼,十四团在右翼,师的指挥所就在离前沿二三里路的地方。还有临时归我师指挥的、武亭同志带领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配置了适当的地方。
刚刚布置好, 侦察员带来了报告,敌人是广西军队第七军的两个师,由夏威率领,离这里已经不远了。以现有的两个团来对付敌人的两个师,兵力的悬殊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的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连续行军,部队减员很大,也很疲劳,更重要的是,从这里到新圩只有十二三里路,又没有工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坚持两三天有把握,4天就有困难了。但是部队的情绪还是高涨的,我和师政治委员十分信赖我们的战士们,为了打击敌人,为了中共中央和兄弟部队的安全,他们会做出奇迹来的。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参谋长胡震同志,他正对着地图出神,显然也是想着同样的问题。听了我的话,他把拳头往桌子上一砸:“让他们来吧,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到新圩!”
他的信心也有力地感染了我。我们一道给军团首长起草了一份电报:保证完成任务!
一切准备就绪,敌人也赶到了。敌人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他们正沿着大路急进,要想快些赶到新圩,来控制我们渡河进路的左翼,但是却被我们这只“铁拳”迎头挡住了。
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敌人在猛烈的炮火、机枪掩护下,向我们前沿阵地猛扑。我走出指挥所,站在一个山头上,向前沿阵地观察。指挥所离前沿不过1.5公里,在望远镜里一切都清清楚楚,敌人的排炮向我们前沿猛击。一时,卧在临时工事里的战士们全被烟尘遮住,看不见了。敌人整营整连暴露地向前沿冲击,越走越近。但是我们的前沿还是沉寂着,仿佛部队被敌人的炮火杀伤完了。但是,当敌人前进到离我们只有几十公尺时,突然腾起了一阵烟雾——我们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就像从土里钻出来似的,追着溃退下去的敌人的屁股射击。“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炸开来。敌人的冲击垮下去了。这个情景使我想到不久以前我们师所进行的高虎垴战斗。那时,我们的战土们也是这样杀伤敌人的。从敌人溃退的情况来看,我们给敌人的杀伤是不小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事,在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下,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第一天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过去了,从第二天拂晓起,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冲击,并以小部队迂回我们。 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全部战士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伤亡增多了,一列列的伤员从我们身旁抬到后面去。十四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 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3个营长2个牺牲,全团伤亡约500人。
团、营指挥员有这样多的伤亡,部队的伤亡是可以想见的。而在当时各团人数并不充实的情况下,一个团伤亡五六百人,也说明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部队还在顽强地坚持着。
这样,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
“‘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几乎每一通电报都要求我们“继续坚持”。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繁重的,稍有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圩,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我也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后方机关是太庞大了,从五次反“围剿”防御失败以后,仓促地转入长征,又不好好地精简组织,坛坛罐罐什么都带上,使得我们的行动迟缓,有些能够摆脱的形势也摆脱不了,不能主动歼敌不说,现在还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掩护这庞大的机构转移,我不由得暗自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步, 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
我和钟政委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走到参谋长身边,告诉了他各团的情况:“十五团团长白志文牺牲了,政治委员罗元发负伤了。”我说:“你去负责,去组织他们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失掉!”他严肃地点点头,没有说什么。我知道,在这种严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接着抓起电话找十四团的黄冕昌团长,我要他适当收缩一下兵力,把团的指挥所转移到我们师指挥所位置上来。
敌人的机枪、炮火已经打到师指挥所旁边来了。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我这里,他刚来到,十五团就来了电话,他们报告,师参谋长胡震同志牺牲了。他是在刚才反击敌人的一次攻击中指挥战斗时牺牲的。
我手捏着电话机愣了好大一会,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牺牲了。胡震同志到这师里还不久,但我们相识却很久了,早在瑞金红校学习时,我们就在一起。 他年青、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但是,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了。
我硬压住自己痛苦的心情,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钟政委,也告诉了黄团长。接着,向黄团长谈了谈中央纵队渡江的情况,并严肃地交代他:“无论如何不能后退。”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战斗开始时,胡震同志用那响亮的湖南口音说过的话,我重复了它一句:“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到新圩!”
可是,当我刚刚到达新的师指挥所时,又接到了报告,黄冕昌同志也牺牲了。这时已是下午,我们已整整抗击了两天,中央纵队还在过江。现在两个团的团长、政治委员都已牺牲或负伤了,营连指挥员也剩得不多了,负伤的战士们还不断地被抬下来。但是,我们是红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我们的战上们在“保卫党中央”这个铁的意志下团结得更紧,伤亡的指挥员有人自动代理了,带伤坚持战斗的同志们越来越多……我们以拼死的战斗,坚持着第三天更险恶的局面,阵地仍然是我们的。敌人被困在这几平方里的山头前面,不能前进!
下午4时许,接到了军团的电报:中央纵队已突过了湘江,正向龙胜前进,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团命令我们把防务移交给六师,部队迅速过江。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我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紧紧握住钟政委的手:“好,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过江去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我一面等待着六师的到来,一面向部队发出了准备撤退的命令。
事情已经过了许多年,仍然不能磨灭我对于这次战斗的深刻印象:无论敌人何等的凶恶、强大,要想消灭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忘记“左”倾分子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由于他们惊惶失措的逃跑主义,在这样大的战略转移中,不能主动灵活地歼灭敌人,行动迟缓,只以消极的防御作战来被动应付,致使我们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我更不能忘记那些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他们以自己的胸膛阻击敌人,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烈士们永垂不朽!文
(李天佑,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