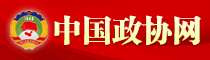- 孙大伟看望慰问离退休副省级老同志
- 自治区政协举行2026年离退休同志迎新春团拜会
- 徐绍川赴防城港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 黄俊华赴柳州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 钱学明赴桂林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 王乃学赴北海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章士钊与陈独秀两人交往密切,早年曾一起革命,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后,两人因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但在个人感情上仍然彼此关心,诗书往来不绝,私谊长存。1932年,陈独秀被捕,章士钊多次出庭为陈独秀辩护,时人称章士钊“有古义士之风”。章士钊晚年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 一文中曾说: “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 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陈独秀之所以难交,主要是因为他个性太强。对于陈独秀的个性,章士钊曾说:“陈独秀……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又说陈独秀如“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此评论中肯,非深知陈独秀者是道不出来的。
抗战时期, 陈独秀息影山乡,章士钊寓居重庆, 两人诗书往还, 简牍不断, 相互关心, 相互慰藉, 谱写了一段晚年友情愈笃的佳话。
爬山涉水探望陈独秀
1938年3月,南京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等人欲引诱章士钊入伙,遭到严词拒绝。为了摆脱梁鸿志等人的纠缠,9月,章士钊离开上海远走香港。冬天,在香港的章士钊接到国民参政会通知,请他赴渝出席国民参政会。12月,章士钊抵达陪都重庆,最初住在国府路政乐庐,数月后,国民政府安排他住进了重庆上清寺中山三路聚兴新村五号,陪他同住的是大儿子章可(妻子吴弱男仍住在香港,二夫人奚翠贞带着章含之在上海)。家里有厨师、勤杂人员等侍候,全部开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这里是政府的一个高级招待所,五号是章士钊住,六号是贺耀祖住,七号是程潜住。三家都是湖南人,因此相互间走动较为密切。日常往来的骚人墨客有沈尹默、于右任、潘伯鹰、高二适及汪东等。这群饱学之士还组织了一个岷江文会,又曰“饮河诗社”,不时聚在一起吟诗作赋,唱酬应答。
一天,章士钊读到潘赞化写的《访仲子鹤山坪》诗后,想起了远在穷乡僻壤的老友陈独秀,他感慨万千,立马赋诗一首《和赞化访仲子鹤山坪依韵》:
江津已是楚人隈,百里乡音狎往来。
犹向林丘寻旧雨,各禁云鹤试诗才。
布衣卅载欣无恙,大弩千钧孰为开?
知我向平情未了,愿隳门弟自相媒。
诗中写了潘赞化早年参加革命,热心为他儿子章可执柯作伐的事,更写出了章士钊想到江津拜访陈独秀等旧友、 共述衷曲的心情。
潘赞化,安徽桐城人,曾与陈独秀共同组织爱国学社,辛亥革命后担任过芜湖海关监督。他也是章士钊的朋友,当时在江津国立第九中学任总务主任,陈独秀的小儿子陈松年在他手下工作。他喜爱诗文,写过不少诗词,经常去看望陈独秀。章士钊正是通过他不时了解到陈独秀当时的情况。
章士钊是什么时候去探望陈独秀的呢?笔者所看到的资料有三种说法:一是袁景华著《章士钊先生年谱》载“一九三九年 58岁……和潘赞化到鹤山坪访仲子(陈独秀)”;二是白吉庵著《章士钊传》载“章士钊到重庆后,也曾去江津看望过陈独秀;不时遣其子章可去问安,书信往来不断。这年夏天,陈的住宅被窃去衣被等物十余件……”三是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中提及陈独秀于1940年8月3日给成都杨朋升的信中写道:“……敝寓昨失窃,窃去衣被等十余样……”从白吉庵的行文看来,他认为章士钊是1940年去探望陈独秀的。但是,在同一本书《章士钊传》的附录《章士钊年表》里,他却又给出了另一种说法“1941年……是年曾到江津看望过陈独秀”。鉴于这三种说法都没有给出有力的历史依据,章士钊探望陈独秀的具体时间有待厘清。但这件事本身是确凿无疑的,地点江津鹤山坪也是确凿无疑的,有章士钊的诗作为证。
王葆斋,安徽金寨人,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任三十三军军长参谋长。北伐结束后,王葆斋于1932年回皖,先后任合肥首席县长、芜湖专员和贵州独山专员。王葆斋在职期间利用手中权力,曾经3次营救过中共地下党员。王葆斋与陈独秀出于乡谊,关系密切,陈独秀的革命思想和行动不见容于当局,屡遭当局忌恨。一次,当局企图加害于他,王葆斋闻悉后,立即设法透信给陈独秀,使其免遭毒手。抗战时期,王葆斋在重庆主持安徽旅渝同乡会,与隐居江津的陈独秀时有过从。于是,章士钊便找到王葆斋,约他一同前往鹤山坪看望陈独秀。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陈独秀生平二三事及其他》一文载:“据王葆斋生前谈,他曾和章士钊相约去江津看陈独秀。事先由章士钊找了蒋介石侍从室,取得同意,才去江津。在江津与陈独秀晤谈后,陈送他们一程,不再前走,说,我只能到此为止,不能再越雷池一步了。这也足可说明,陈在江津是不自由的。”
陪同章士钊、王葆斋前往鹤山坪看望陈独秀的还有潘赞化。当时他在江津长江对岸的德感坝国立九中任职,与陈独秀来往频密,熟悉去鹤山坪的路径,章士钊自然要约他同行。他们从江津乘木船逆江而上,到五举沱码头下船,章士钊已是六旬老人,体力有些不支,长长的15公里山路便以滑竿代步。来到鹤山坪石墙院,见到40年交情的老友,自然是悲喜交加,诸多往事袭上心头,免不了一阵欢欣和激动。在书房摆谈了一阵后,陈独秀带着他们来到院外的山野间,指点河山,明察风物。章士钊满足了探视老友的心愿,因不能在此久留,他们要返回江津过夜,两位老友就此依依惜别。
章士钊返回重庆后,心中对陈独秀念念不忘,石墙院对面山上的飞仙洞,荷叶田田摇曳的荷塘,展翅高飞的鹤群,清翠欲滴的竹林,还有那呼啸而过的山风,依然在他脑海里翻腾,于是他展纸提笔,作诗《怀独秀鹤山坪》:
幽人忘老住江隈,门对飞仙洞口开。
狮子风翻千里吼,鹤见云送近山来。
清荷接眼浑生爱,恶竹横胸定欲裁。
气类试看潘正叔,衰年异地莫轻哀。
章士钊的朋友,也是章士钊《孤桐诗稿》的保存者李根源,在这首诗的后面注解道:“先生与陈独秀文旧笃,故赠诗颇多。鹤山坪在江津县,距飞仙洞甚近。正叔谓潘赞化。”
这首诗的首联和颌联,写了陈独秀居住的环境:江边,面对飞仙洞,风大,仿佛看到鹤在云中翱翔,寓意刚毅坚强的精神;颈联写了他们当时眼前的景致;尾联则以潘赞化勇于面对现实、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尽心竭力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精神,安慰并鼓励老友陈独秀莫要颓丧莫要悲哀。
为陈独秀延医治病
陈独秀身患沉疴由来已久。还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因第二次被捕入狱,“久失自由,因而发生胃病”;1920年代,他又两次入狱,加上为革命风风火火地奔波劳累,致使未能得到彻底根治的胃病不时复发,这期间他还得过伤寒病。之后,陈独秀又患上了高血压,至1932年第五次被捕时,病状已很明显。他致书章士钊,请他找一位上海名医来南京狱中为他治病。
章士钊赓即约请上海名医黄钟医师,专程赴宁为他治病。当陈独秀蛰居江津之初,上述两病又时刻纠缠着他,且有加剧之势,病情正如当时他的老友汪孟邹向胡适介绍的那样:“近得他来信,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虽然老友邓仲纯医生常来为他治病,但效果却总是不太显著。邓仲纯说,重庆有名医周伦、曾定天二人对治疗高血压病有独到之处,建议陪他去重庆治疗。于是陈独秀便给章士钊去信,请他联系重庆的名医为他诊治。章士钊找到了重庆最好的西医医院——宽仁医院,这是基督教卫理公会派出的美国人马加里医生和英国伦敦传道会医生创办的重庆第一家西医医院,坐落在下石板街戴家巷口。1939年初,为躲避日机轰炸,宽仁医院奉命部分迁往市郊的歌乐山云顶寺山麓,在那里设立医疗分部。
1940年1月4日,陈独秀夫妇由鹤山坪到江津县城,等待章士钊的消息。不久,章士钊来信说,为陈独秀看病的医生去了歌乐山,要陈独秀推迟几日到重庆。1940年2月6日,受北大同学会委派来照顾陈独秀的何之瑜陪同陈独秀、潘兰珍夫妇到了重庆,直接住进了章士钊为他联系好的宽仁医院。
春节要到了,章士钊请陈独秀一行人去他家过春节。当时章士钊已从国府路政乐庐搬到中山三路聚兴新村5号住。陈独秀摇头说:“乱哄哄的时候,饭都吃不好,还过什么春节。”章士钊知道陈独秀脾气,也不勉强他。两人谈到成都的杨朋升,章士钊说:“杨先生给我刻的印章样本,我已收到了,你替我谢谢他。”陈独秀感慨地说:“杨先生真是热心人,三番五次地支持我,我现在欠债太多。”章士钊点点头说:“你安心养病,不要想那么多,出院后,到我家住一阵子。”陈独秀点头说:“我这次来,打算在医院住十日,在朋友家住十日。”
这时何之瑜进来,叫他们说话轻些,医生要来给陈独秀检查。
陈独秀住2号病房,医生认真仔细地检查了他的血压、心脏和肠胃,医生看病时脸部表情凝重,对陈独秀说:“你的病,不在药好药孬,根治在静养。”何之瑜听医生话中有话,便跟随医生走出病房,对医生说:“陈先生是个名人,请医生一定要尽力。”医生说:“知道、知道,记得陈先生以前在北大干过什么事?”何之瑜说:“任过北大文科学长。”医生点点头,说:“听陈先生自己说,他是坐牢时把身体坐坏的。陈先生这个病与精神不稳有关,回去一定要安静休息,不要再过问政治。”何之瑜点头称是,问:“你看陈先生的病很严重吗?”医生凝视着何之瑜,低声说:“你是他的学生,可以告诉你,陈先生可能活不了3年。”何之瑜大吃一惊,问:“有这么严重吗?”医生说:“陈先生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何之瑜颔首道:“请医生千万不要告诉陈先生和陈太太。”
正月里的一天,包惠僧来看陈独秀。包惠僧当时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参事,薪酬低且有职无权。陈独秀躺在病床上劝他说:“不要再认死理,找找人,搞个一官半职。现在物价这么高,守在那里总不是事。”包惠僧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说:“先生来重庆一趟不容易,出院后,我来接你去我家住几天。”当时包惠家住陈家桥。陈独秀说:“年老多病,行动不便,还是不去了。本来打算到行严(即章士钊)家住几天,也不想去了。”包惠僧问:“怎么不去了?”
陈夫人潘兰珍插嘴说:“重庆太吵,先生烦燥得很,天天吵着要回去。”
2月20日上午,陈独秀离开医院,没有去章士钊家住,直接乘船回到江津。经过宽仁医院两周的精心治疗,陈独秀的病似有好转,于是,回到江津的次日,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给杨朋升去信说:
在渝病院中曾寄上二函,已达左右否?渝市医院,不易(宜)久居,弟已(于)昨日午后三时回抵江津,乘船八小时,病势并未增剧,想已稍稍减轻矣。知注特闻。
互相关怀唱合不绝
原住在江津邓仲纯家的陈独秀,一来因天气燠热,不利养病,二来因夫人潘兰珍与邓仲纯妻相处不睦,1939年7月,在江津富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帮助下,迁居江津大西门外10多公里的鹤山坪施家大院(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家)。但因施家儿童吵闹,不利陈独秀静养,8月,应清朝进士杨鲁承遗族之请,迁居杨鲁承旧居石墙院,一面帮助整理杨氏的文字学遗著手稿,一面专心写作《小学识字教本》。进入秋天,绵绵秋雨动相思,陈独秀不由得怀念起老友章士钊来,他写了一首五律《简孤桐》,诗云: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兮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
陈诗在怀念友人的同时,又写出了在战乱中无处安身的焦虑。贫病交加是当时陈独秀真实生活的写照,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说:“他们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是些破桌子破椅子,生活很苦。”但并不因生活的艰困而沉沦,“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不仅表达了陈独秀对与章士钊友情的珍惜,更表达了他对抗战胜利充满期望。
收到陈独秀的这首诗后,章士钊很快写了《答独秀》的诗:
仲子绝豪望,独居鹤山坪。
闻看岭头云,偶作寄友诗。
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
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
往事在俄顷,后事吾岂知!
还讯山中人,尔鹤吐何词?
诗的前面部分陈述了陈独秀无奈的现状,与陈独秀相比,章士钊当时的处境是比较优越的。但他毕竟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士,对时局的发展并不了解,而曾经的革命领袖陈独秀虽已息影政坛,但他有洞察时事的智慧,因此,章士钊在诗中提出了欲知今后战事如何发展的反问。
陈独秀在石墙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冬季来临,他又觉得这里山风凛冽,寒气袭人,不宜养病。此事传到章士钊那里,章士钊觉得陈独秀的处境实在太差,又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改变环境才行,于是邀陈独秀来重庆与之同住,并附去《劝仲甫移居》诗一首,诗云:
山中消息使我惊,血如山重耳雷鸣。
深山寒气不任受,友劝移居非恶声。
我忝廪食专一室,足有隙地招友生。
记否昌寿里中味,黑衣白虱相纵横。
抹除四十年间事,尔我再起用笔耕。
连床虽无苏张伴,老潘隔江仍可面。
溥泉官大不可唤,沐波勤口定常见。
干戈满地两秃翁,几时聚散何须算。
嚣俄小说应重翻,快来与我共笔砚。
这首诗写得文情并茂,情真意切。“记否昌寿里中味,黑衣白虱相纵横”,说的是当年(1903年)他们在上海昌寿里共办《国民日日报》的事。1934年,陈独秀、章士钊的朋友王森然出版了一本《近代二十家评传》,其中记述了陈独秀、章士钊等在一起的生活往事,其形貌跃然纸上:
先生在沪与章秋桐(章士钊)、张溥泉、谢晓石公立国民日日报。与秋桐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秋桐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秋桐骇然曰:仲甫!何也?先生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此时他们共同的朋友苏曼殊、张华飞都已作古,再也不可能有1914年在日本时与苏、张连床在一起休憩的美好过去,唯有老潘(赞化)隔江而住,可以随时见面。潘赞化与章土钊都劝陈独秀换个生存环境,最好是去重庆与章氏同住,如同当年在昌寿里。“嚣俄(雨果)小说应重翻,快来与我共笔砚”,这两句诗表明章士钊对两人的重聚充满了期待。但陈独秀却没有接受章士钊的盛情邀请。
1941年8月2日,陈独秀鹤山坪寓所被盗,消息传到重庆,章士钊甚以为念,作《独秀遇盗诗》一首,表示慰问:
乱世百不道,盗道亦互轻。
朱门不敢动,翻劫鹤山坪。
坪中伊何人,寂寞一陈生。
陈生旷无有,残稿东西横。
并此且略去,赋意吾难名。
恭元不可贺,好爵非所萦。
吾异洛阳守,贼曹非所令?
聊以诗慰之,为媵故旧情。
此情不可市,敢曰压子惊。
诗的前半部分谴责了乱世盗贼亦不道,然后转而对陈独秀作了一番安慰。次年,闻被盗之物追回了部分,章士钊又有《寄独秀》诗云:
西风吹彻古渝州,遥望幽栖动客愁。
长物有时令盗惜,不才何用遣官忧。
河山嫩与人期老,蜀洛看同水并流。
偶忆何郎归骨句,未知曾过几春秋?
1941年,日机对重庆进行了狂轰烂炸,章士钊上清寺寓所被炸毁,弄得章士钊居无定所。陈独秀了解到章士钊这一境况后甚感忧虑,特致信关怀问候。对此章士钊深受感动,慨叹之余,专门写了一首诗《独秀书来以吾寓被轰炸为忧》,以示对老友的不胜感激,诗曰:
饭颗山间讯,浑疑禹穴荒。
盯猜应不远,欲杀似难防。
人鬼艰为界,虫鱼愿徒乡。
洞门新活计,歧路旧佯狂。
贾谊欲无舍,周颐何处墙。
卌年梅福里,回首自凄凉。
这首诗表明了章士钊的达观和大度:日机想炸就炸吧,我们防不胜防,好在“贾谊欲无舍,周颐何处墙”,充其量沦落到我们当年在梅福里办《国民日日报》时那般处境。从中可看出陈、章二人交情之深,友谊之厚,即便身处困境,仍然互相关怀,互相慰藉,并以早年参加反清革命的事迹来共勉。
1941年6月1日,章士钊在《初出湘》一诗中,追述了他与陈独秀早在1903年就开始的友谊。诗中写道: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
陈独秀困居山乡,精神孤寂,疾病缠身,生活艰难,希望与外界沟通,与老友神交。章士钊深深理解并同情陈独秀的遭遇,便常常以诗来抒发自己对老友的牵挂和怀念。所以,在陈独秀晚年,他与章士钊的诗书往来就比较频繁。下面的两首《寄独秀》,就是章士钊当时心境的写照。诗曰:
其一
四十年间事,轻风并作声。
骁腾梅福里,蹩躠鹤山坪。
也听诗流落,何妨世浊清。
秃翁森两个,隔水话无成。
其二
屏迹衰颜惯,怀哉愿薄游。
地宜违贼火,屋欲近书楼。
吾意亲灵岳,平生本楚囚。
应须同放棹,一访石船秋。
从现在保存的诗文看来,在陈、章两人的唱和中,主要是章诗多一些,这恐怕与陈独秀晚年生活艰难,处于贫病交迫之中有关,再者就是陈独秀忙于撰写《小学识字教本》而无暇作诗,与友朋交往常以短简代诗。
1941年,章士钊应湖南老乡、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警备司令兼桂林行营交通总指挥蒋锄欧之邀到桂林游玩。7月下旬,章士钊携三夫人殷德珍同行,抵桂后就住在市内城东侧塘前街蒋宅。章士钊此行的目的一来是为了躲避重庆炎热的夏天,到风景秀丽的桂林避暑,二来是借此机会可以与他在桂林的侄儿见见面,以解平日思念之情。
章士钊到桂林后与一些文化名人如柳亚子、朱荫龙、封鹤君等人常相过从。经柳亚子的介绍,章士钊认识了当地的朱荫龙,并向他学习填词。在朱荫龙的指导和帮助下,章士钊在桂林近半年的时间里填了很多词。
桂林有座独秀峰。章士钊在游览时由“独秀峰”想到困居鹤山坪的“怀宁客”陈独秀(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在峰前久久徘徊,不忍离去。随后便填词一首《念奴娇·独秀峰怀古》, 表达了自己对友人的怀念。词曰:
靖江王府,三百年不靖,究缘何物,更溯人前,都说是,太守风流欲绝。半壁河山,寄奴经济,气节胡从说。读书堂下,试问谁是人杰?
步到独秀峰前,低徊身世,想起怀宁客。自异求同冰炭性,人已一时应灭。今日迟来,坐观池水,干我无毫发。此岩千古,不须妄记年月。
一行人在沿漓江西上的时候,章士钊在漓江山水甲天下的优美景色中,睹物思人,想起了重庆诸友,便写下《念奴娇·怀重庆诸友》,词曰:
漓江西上,是几时,不见渝州烟雨。闻说日长阴洞里,贼火今年如许。四面山明,一肩人瘁,人被山留住。却怀诸友,此时分散何处?
谁管独秀峰高,延年魂在,读得书如故。作客漫将诗骨换,稍稍寻声按谱。潭水深汪(旭初),东阳瘦沈(尹默),谁与商今古。开缄试看,渠依新学言语。
词中不仅怀念陈独秀,还怀念他已壮烈牺牲的儿子陈延年,赞他英魂千古。
后来,章士钊读到一首沈尹默答陈独秀的诗。此诗使他不由再次思念在鹤山坪的陈独秀。回想当年陈独秀那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慨, 联想到此时陈独秀的落魄景况,章士钊真是感慨万端,写下一首《读尹默答独秀诗》:
久阔陈生讯,忽见沈子诗。
意如矢过楹,只恨拙言辞。
凄绝鹤山风,遥对鹰崖吹。
谁云不识路,翻怯相逢时。
我行入衡岳,频梦相扶持。
盗贼既塞途,老病心亦危。
当年豪意严,津梁已告疲。
不须重搔首,天意吾安知。
传噩耗诗词寄哀思
章士钊请来的宽仁医院的医生看准了陈独秀的病,他一语成谶。陈独秀回到江津鹤山坪石墙院后,因住在偏僻山乡,缺医少药,医疗条件极差,虽经当地土郎中及好友邓仲纯医生多方医治,甚至弄了些农村流行的偏方来服用,但终究回天乏术,奇迹未能出现,离开宽仁医院后,他只活了2年零3个月,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江津鹤山坪石墙院。当时,章士钊在上清寺范绍增公馆与陪都上层人士玩兴正浓,忽报老友仲甫遽归道山,章士钊顿感悲痛异常。随后的一段时间,章士钊足不出户,整日闷闷不乐,有时翻阅他的那一堆书稿,仿佛想要从中找寻出那些与陈独秀交往的蛛丝马迹。数日后他终于振作精神,以浓墨重笔,深情地在“孤桐用笺”上写下了《忆旧游·陈独秀挽词》, 词章全文如下:
记倾心癸好,返国丁年,尔我同携(岁次癸卯,君返自东京同讲革命)。未计危楼窄,有红灯似豆,白虱如脂(君羊毛衵衣半年未换,春尽脱去,白盖黑地)。此情未堪追忆,风雨晦冥时。叹瘦骨崚峋,言皆断制,态绝犹夷。凄其。系人处,是结客千金,菲食牛衣。馎饦餐来惯,看焦麻飞落,手蘸无遗。好汉不求人谅,艰苦自家知。略师友平生,斯人亘古无此期(君乏食时购胡饼两枚充饥,芝麻落地以手拈取送入口内,傅沐波屡见之)。
章士钊回首往事,写出了一个活脱脱的不畏艰困、秉性刚毅的革命家形象,写出了他心中真实的陈独秀。
1943年6月,章士钊的一部重要著作《逻辑指要》由重庆时代精神社出版,了却了一桩心愿,章士钊自然感到心情舒畅。7月,重庆酷暑来临,章士钊应丰都门人冉仲虎之邀往峨嵋山避暑,同行者有潘伯鹰。舟行至泸州,被该县士绅挽留,一住就是月余。9月初,天气渐凉,章士钊诸人的游兴已尽,故终止了峨嵋之行。
章士钊在泸州期间写下了许多诗词,后由门人冉仲虎编辑成册,题曰《游泸草》。该册集诗词约50多首,由大同印刷社印行,流传于世。其中有一首《过江津怀独秀》系怀念陈独秀的七绝,感情真挚,悲惜之情溢于诗外,诗曰:
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
我是山阳江上客,怕嫌闻笛失寻阾。
可见陈独秀病逝鹤山坪一年后,章士钊仍然心怀老友,船过江津,遥望康庄前坡的一座新坟,触景生情,无限哀伤。据当时在章士钊身旁侍坐的潘伯鹰记云:“舟过江津,行丈(章行严,即章士钊)有诗吊陈独秀鹤山坪葬处。”章士钊倚栏哀伤的模样潘伯鹰将之形容为:“丈人舟行过,倚栏久哀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