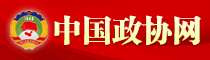- 孙大伟看望慰问离退休副省级老同志
- 自治区政协举行2026年离退休同志迎新春团拜会
- 徐绍川赴防城港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 黄俊华赴柳州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 钱学明赴桂林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 王乃学赴北海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铭记了一师的教诲
——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 张双棣
2020年是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收到王力先生的儿子王缉志先生的电话,他说,《文史春秋》杂志要出一期纪念国学大师王力的专刊,邀请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而我也正有这种意愿,自然就满口应允了。
前不久,见到知名作家、摄影家邹士方于2019年在《文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回忆王力先生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王力教授很喜欢让我为他照相,每次我把放大的照片送给他,他都十分高兴。记得我拍过一张他和他助手张双棣的工作照片,他十分满意;后来我放大了一张十二英寸的送与他,他把它挂在自己的房间中。”邹先生所说的这幅照片,现在正挂在我的书房内。这幅照片,是王力先生去世后,他的妻子亲自从墙上摘下来,送给我留作纪念的。现在再看这幅照片,心情还如同那时一样激动,这不禁让我回想起跟随王力先生学习和工作的情形。
1970年代末,国家教育部为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的老专家配备助手,协助他们工作。我有幸于1979年9月担任王力先生的助手,协助他从事科研工作。与其说是协助王力先生工作,不如说是在工作实践中跟着王力先生学习。我跟王力先生在一起工作了7年,直到他去世。我在王力先生家里有一个小的工作间,便于和他一起工作,也可以随时聆听他的教诲。
当时,王力先生正在修订《汉语史稿》的语音史,说是修订,其实是重写。原来《汉语史稿》的语音部分是以《广韵》音系为纲,上考古音,下推今音;而修订版要写的《汉语语音史》则是按照时代分成先秦、汉代……明清、近代9章,每个时代都是用那个时代的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分析。我就负责按照王力先生的要求,帮他找他不便到图书馆去找的资料,这对我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这期间,王力先生多次对我讲,作科研材料很重要,有了材料,才好作分析,得出的结论才靠得住。这就是王力先生后来常说的,做科研工作,一是要占有材料,二是要有科学头脑。材料是基础,科学头脑是逻辑思维能力,二者缺一不可。王力先生的这个思想一直指导着我的科研工作。
王力先生在写隋唐语音史部分的时候,他觉得唐代何超的《晋书音义》很有价值,要我对其中的反切(反切是古人创制的一种注音方法,用两个汉字相拼给一个字注音,切上字取声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作一些考察分析。王力先生很耐心的告诉我如何分析每一个反切,从反切所体现的声母和用韵去整理它的语音特点。我遵照先生的指导,写了一篇《晋书音义反切考》,这是我第一次写这类文章,自然写得有些粗疏。给王力先生看了之后,他觉得还可以,还帮我作了简单的修改,并推荐给《语言学论丛》。《论丛》答应采用。此后不久,我见到《中国语文》发表了邵荣芬先生分析《晋书音义》的文章,比我写得详细深入,且得出的结论有些也近似。我就跟王力先生商量是否将我那篇从《论丛》撤下来,王力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那篇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写作过程中,王力先生对我的指导和教诲,是我受用终生的。
1980年代初,王力先生提倡汉语史研究要重视专书语言研究。他多次对我讲,汉语史研究要以专书语言研究为基础,要研究专书词汇、专书语法,将同时代的专书词汇、专书语法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特点。王力先生还鼓励我作一本专书研究。我当时提出是否可以作《吕氏春秋》,我提了几个理由,王力先生说可以,于是我选定《吕氏春秋》作专书语言研究。因为考虑工作量太大,在协助王力先生工作的同时,我独自一人完成研究有些吃力,就约了我的3位大学同学一同完成。我们先作校勘、译注的工作。首先要读懂古人的书。王力先生跟我说:“古人的书,尤其是先秦的书,大部分都有汉唐人的注释。因为汉唐离先秦不远,他们的注可以作为我们读先秦著作的钥匙,要重视这些注释。但在作语言研究的时候,也不能迷信这些注,古人往往缺乏历史的观念,不能从历史的角度解释词义。”王力先生的这些话,成为我专书语言研究的指导思想。我们做完《吕氏春秋译注》,将《前言》和部分样稿给王力先生看,请他提提意见。王力先生用铅笔改了几个字,并热情地为我们写了序,在序中给我们很多鼓励,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之后,我们接着作《吕氏春秋词典》。我将词典的基本构想呈请王力先生指点。我们的构想是以上古音为纲,将词义系统与语法结构结合起来,也就是将词义描写与用法描写结合起来进行阐述,这样,可将语音、语法、词义融为一体。我将部分样稿拿给王力先生看,他很赞成我们的做法,特别提醒我们,确定复音词、确定词类是很麻烦的,一定要考虑周全些。王力先生还对样稿做了修改,并欣然应允当这部词典的顾问。但特别遗憾并令人悲痛的是,王力先生没有看到这部词典的出版就离开了我们。此后我又写出了《吕氏春秋词汇研究附吕氏春秋韵谱》。可以说,我们的《吕氏春秋》语言研究是在王力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的。

王力教授晚年仍笔耕不辍,从事学术研究与写作(1981年)
还是1980年代初,山西人民出版社要出版王力先生在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我在整理旧稿时,看到上面有梁启超先生的评语,也有赵元任先生的批语。梁先生的评语多是赞扬的话,如在扉页上写的“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赵先生的批语多是指出文章不足或提出建议,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王力先生说,梁先生的嘉许和鼓励,是让研究生树立信心,敢于攀登学术的高峰。赵先生的批评是让研究生更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王力先生特别提到其中赵元任的一句批语:“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他指着这句话对我说:“赵先生这句话讲得很深刻,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我们作汉语史研究,切不可轻易说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域没有某个语言现象,因为我们没有把那些材料都读完。要下一个结论,必须得有充分的证据。赵先生‘言有易,言无难’六个字,一直是我研究工作的座右铭,你也得记牢这句话。”听取王力先生的教诲,受益良多,我便也将这六字作为终身的座右铭。后来我在指导研究生时,也常用赵先生的六字真言告诫他们。
当时,王力先生以80多岁的高龄,每天上午一坐就是4个小时,我觉得这样太累了。所以经常在上午10时左右扶他到客厅里坐坐,陪他聊聊天,让他稍稍休息一会儿。聊天中,王力先生除了讲讲他的故事,也常讲一些学术问题,虽然是只言片语,对于我来说却是十分珍贵的。有一次聊起清代朴学,王力先生对段玉裁赞赏有加,说他有历史观念,能看出不同时代的词义变化。又说,清代乾嘉学者尊重材料,发议论都能以材料为依据。这就是所谓的朴学精神。这些对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记得有一次说到著作的出版,王力先生说,对某些问题有新的想法,写出书来,不必等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再出版,有百分之七八十就可以出版。出版后,可以得到读者的意见,就可以修订提高;想一下子做到十全十美,很难,甚至不可能;再者,这样也可以占先机,抢占市场。王力先生这个看法,初听十分震撼,仔细一想,真是至理名言,让我茅塞顿开。我后来有的书,就是遵循他的话去做的,在不断的修订中逐步完善起来。
1981年,北大教研室安排我去给学生上古代汉语课,王力先生同意了。他说,去接触接触学生,了解一下他们对古代汉语的想法。王力先生又说,教学一定要和科研结合起来,大学跟中学不一样,中学老师可以按照教育部的教材去教,大学老师则要靠自己的科研成果。中学老师是买书教学生,大学老师则是要写书教学生。王力先生的话,太精辟了,一下子把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说得入木三分。王力先生自身就是教学与科研完美融合的最杰出的典范,他的很多著作都是教学的产物,如《汉语史稿》《中国语言学史》等等,都是先做讲义给学生讲授,在讲授过程中再充实提高,最后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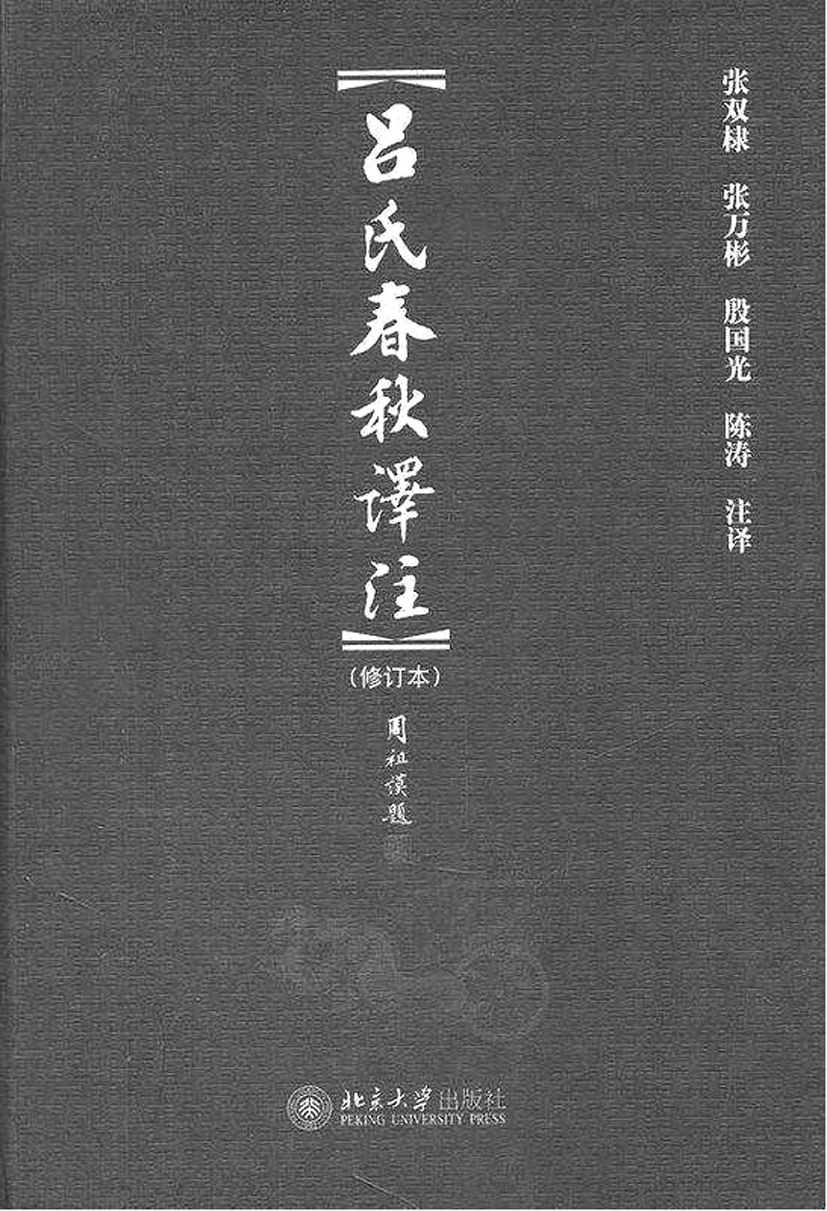
张双棣等人在王力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吕氏春秋译注》
王先生对语言学的执著追求与敬业精神,对我也是一种极大的教育。他一生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到80岁时还豪迈地说:“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他说到做到,他80岁之后还完成了好几部著作,如《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康熙字典音读订误》,又修订了《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真是硕果累累,这些成果都出自他的勤奋工作。王力先生如此高龄,每天仍工作六七个甚至七八个小时,一直到他去世之前。王力先生自1940年代就一直想写一本理想的字典,1984年他以84岁高龄写作《古汉语字典》。每天伏案笔耕,直到1985年10月,他感觉体力不支,才找来在教研室工作的他的学生帮他完成。大家劝王力先生好好休息一段,可他闲不下来,坚持自己完成手头的卯集,并且还要接着写亥集。
1986年3月,王力先生体力越发不好,总感觉疲劳。我对他说:“亥集您就别写了,我来写。”他答应了。后来他给妻子写过这样一段话:“张双棣愿意替我写下去,我的眼睛不行了,又疲劳,干着急,但是今后做什么呢,一天到晚疲劳……”
没过多久,3月27日,王力先生就因病住进了友谊医院。5月3日,王力先生永远离开了,离开了他的家人,他的学生,他钟爱的语言学事业。王力先生对语言学事业,鞠躬尽瘁,成为我们永远的楷模。王力先生对我的教诲,我会永远铭记在心中,并传授给我的学生,使先生的思想和学术永久地传承下去。文
(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专业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