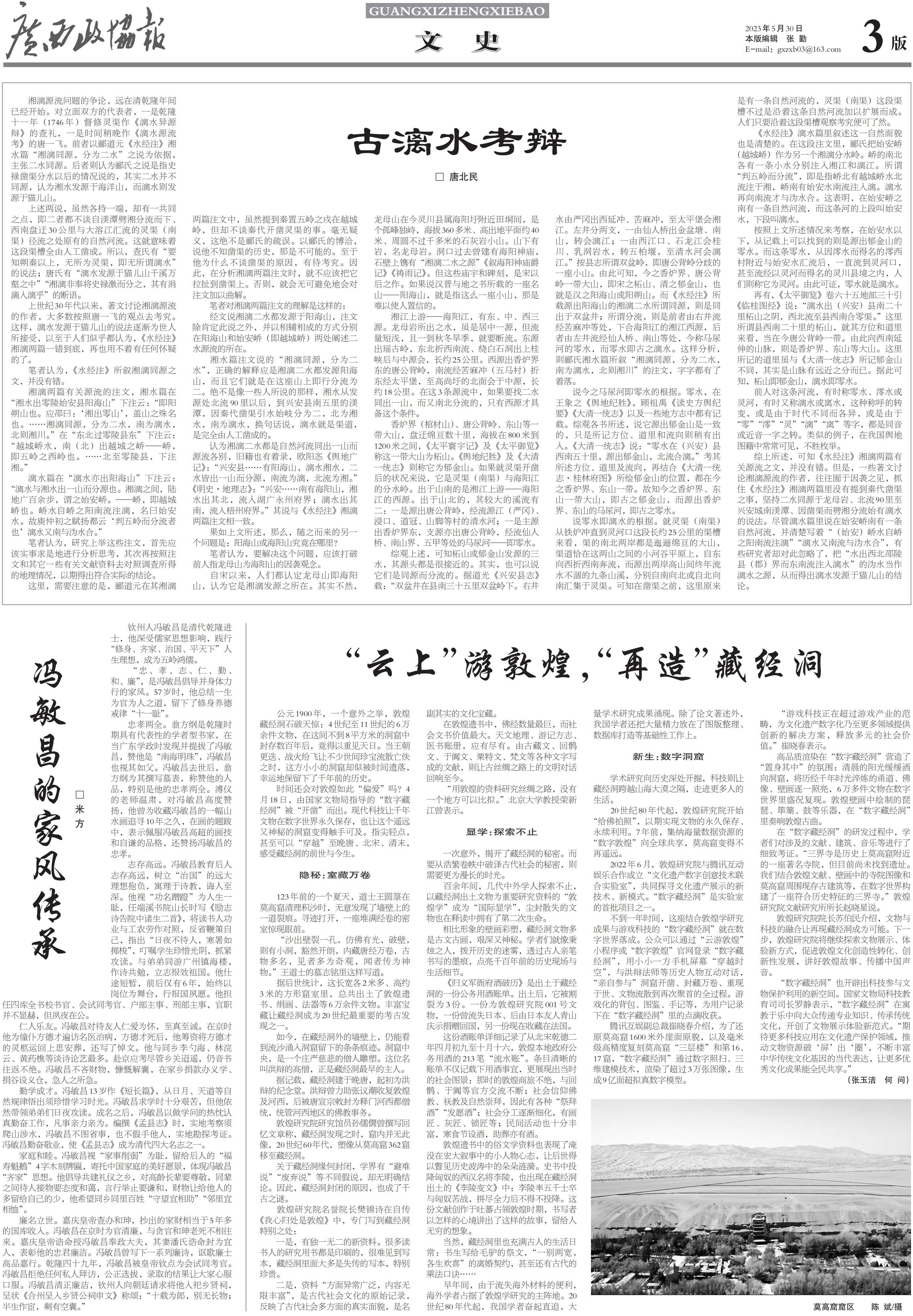古漓水考辩
□ 唐兆民
湘漓源流问题的争论,远在清乾隆年间已经开始。对立面双方的代表者,一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督修灵渠作《漓水异源辩》的查礼,一是时间稍晚作《漓水源流考》的唐一飞。前者以郦道元《水经注》湘水篇“湘漓同源,分为二水”之说为依据,主张二水同源。后者则认为郦氏之说是指史禄凿渠分水以后的情况说的,其实二水并不同源,认为湘水发源于海洋山,而漓水则发源于猫儿山。
上述两说,虽然各持一端,却有一共同之点,即二者都不谈自渼潭劈湘分流而下、西南盘迂30公里与大溶江汇流的灵渠(南渠)径流之处原有的自然河流。这就意味着这段渠槽全由人工凿成。所以,查氏有“要知朔秦以上,无所为灵渠,即无所谓漓水”的说法;唐氏有“漓水发源于猫儿山千溪万壑之中”“湘漓非奉将史禄激而分之,其有涓滴入漓乎”的断语。
上世纪30年代以来,著文讨论湘漓源流的作者,大多数按照唐一飞的观点去考究。这样,漓水发源于猫儿山的说法逐渐为世人所接受,以至于人们似乎都认为,《水经注》湘漓两篇一错到底,再也用不着有任何怀疑的了。
笔者认为,《水经注》所叙湘漓同源之文,并没有错。
湘漓两篇有关源流的注文,湘水篇在“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下注云:“即阳朔山也。应邵曰:‘湘出零山’,盖山之殊名也。……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南为漓水,北则湘川。”在“东北过零陵县东”下注云:“越城峤水,南(北)出越城之峤——峤,即五岭之西岭也。……北至零陵县,下注湘。”
漓水篇在“漓水亦出阳海山”下注云:“漓水与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漓之间,陆地广百余步,谓之始安峤。——峤,即越城峤也。峤水自峤之阳南流注漓,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之赋扬都云‘判五岭而分流者也’漓水又南与沩水合。”
笔者认为,研究上举这些注文,首先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思考,其次再按照注文和其它一些有关文献资料去对照调查所得的地理情况,以期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郦道元在其湘漓两篇注文中,虽然提到秦置五岭之戍在越城岭,但却不谈秦代开凿灵渠的事。毫无疑义,这绝不是郦氏的疏误。以郦氏的博洽,说他不知凿渠的历史,那是不可能的。至于他为什么不谈凿渠的原因,有待考究。因此,在分析湘漓两篇注文时,就不应该把它拉扯到凿渠上。否则,就会无可避免地会对注文加以曲解。
笔者对湘漓两篇注文的理解是这样的:
经文说湘漓二水都发源于阳海山,注文除肯定此说之外,并以相辅相成的方式分别在阳海山和始安峤(即越城峤)两处阐述二水源流的所在。
湘水篇注文说的“湘漓同源,分为二水”,正确的解释应是湘漓二水都发源阳海山,而且它们就是在这座山上即行分流为二。绝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湘水从发源处北流90里以后,到兴安县南五里的渼潭,因秦代凿渠引水始岐分为二,北为湘水,南为漓水,换句话说,漓水就是渠道,是完全由人工凿成的。
认为湘漓二水都是自然河流同出一山而源流各别,旧籍也有着录,欧阳忞《舆地广记》:“兴安县……有阳海山,漓水湘水,二水皆出一山而分源,南流为漓,北流为湘。”《明史·地理志》:“兴安……南有海阳山,湘水出其北,流入湖广永州府界;漓水出其南,流入梧州府界。”其说与《水经注》湘漓两篇注文相一致。
果如上文所述,那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阳海山或海阳山究竟在哪里?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打破前人指龙母山为海阳山的因袭观念。
自宋以来,人们都认定龙母山即海阳山,认为它是湘漓发源之所在。其实不然,龙母山在今灵川县属海阳圩附近田垌间,是个孤峰独峙,海拔360多米、高出地平面约40米、周圆不过千多米的石灰岩小山。山下有岩,名龙母岩。洞口过去曾建有海阳神庙,石壁上镌有“湘漓二水之源”《叙海阳神庙爵记》《祷雨记》。但这些庙宇和碑刻,是宋以后之作。如果说汉晋与地之书所载的一座名山——阳海山,就是指这么一座小山,那是难以使人置信的。
湘江上游——海阳江,有东、中、西三源。龙母岩所出之水,虽是居中一源,但流量短浅,且一到秋冬旱季,就要断流。东源出瑶古岭,东北折西南流、绕白石洞出上桂峡后与中源会,长约25公里。西源出香炉界东的唐公背岭,南流经苦麻冲(五马村)折东经太平堡,至高尚圩的北面会于中源,长约18公里。在这3条源流中,如果要找二水同出一山,而又南北分流的,只有西源才具备这个条件。
香炉界(棺材山)、唐公背岭、东山等一带大山,盘迂绵亘数十里,海拔在800米到1200米之间,《太平寰宇记》及《太平御览》称这一带大山为柘山。《舆地纪胜》及《大清一统志》则称它为郁金山。如果就灵渠开凿后的状况来说,它是灵渠(南渠)与海阳江的分水岭。出于山南的是湘江上游——海阳江的西源。出于山北的,其较大的溪流有二:一是源出唐公背岭,经流源江(严冈)、浸口、道冠、山脚等村的清水河;一是主源出香炉界东,支源亦出唐公背岭,经流仙人桥、南山界、五甲等处的马尿河——即零水。
综观上述,可知柘山或郁金山发源的三水,其源头都是很接近的。其实,也可以说它们是同源而分流的。据道光《兴安县志》载:“双盆井在县南三十五里双盆岭下。右井水由严冈出西延冲、苦麻冲,至太平堡会湘江。左井分两支,一由仙人桥出金盆塘、南山,转会漓江;一由西江口、石龙江会桂川、乳洞岩水,转五柏堰,至清水河会漓江。”按县志所谓双盆岭,即唐公背岭分歧的一座小山。由此可知,今之香炉界、唐公背岭一带大山,即宋之柘山、清之郁金山,也就是汉之阳海山或阳朔山。而《水经注》所载源出阳海山的湘漓二水所谓同源,则是同出于双盆井;所谓分流,则是前者由右井流经苦麻冲等处,下合海阳江的湘江西源,后者由左井流经仙人桥、南山等处,今称马尿河的零水,而零水即古之漓水。这样分析,则郦氏湘水篇所叙“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南为漓水,北则湘川”的注文,字字都有了着落。
说今之马尿河即零水的根据。零水,在王象之《舆地纪胜》,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以及一些地方志中都有记载。综观各书所述,说它源出郁金山是一致的,只是所记方位、道里和流向则稍有出入。《大清一统志》说:“零水在(兴安)县西南五十里,源出郁金山,北流合漓。”考其所述方位、道里及流向,再结合《大清一统志·桂林府图》所绘郁金山的位置,都在今之香炉界、东山一带。故知今之香炉界、东山一带大山,即古之郁金山,而源出香炉界、东山的马尿河,即古之零水。
说零水即漓水的根据。就灵渠(南渠)从铁炉冲直到灵河口这段长约25公里的渠槽来看,渠的南北两岸都是迤逦绵亘的大山,渠道恰在这两山之间的小河谷平原上,自东向西折西南奔流,而源出两岸高山间终年流水不涸的九条山溪,分别自南向北或自北向南汇集于灵渠。可知在凿渠之前,这里原来是有一条自然河流的,灵渠(南渠)这段渠槽不过是沿着这条自然河流加以扩展而成。人们只要沿着这段渠槽观察考究便可了然。
《水经注》漓水篇里叙述这一自然面貌也是清楚的。在这段注文里,郦氏把始安峤(越城峤)作为另一个湘漓分水岭。峤的南北各有一条小水分别注入湘江和漓江。所谓“判五岭而分流”,即是指峤北有越城峤水北流注于湘,峤南有始安水南流注入漓。漓水再向南流才与沩水合。这表明,在始安峤之南有一条自然河流,而这条河的上段叫始安水,下段叫漓水。
按照上文所述情况来考察,在始安水以下,从记载上可以找到的则是源出郁金山的零水。而这条零水,从因澪水而得名的澪西村附近与始安水汇流后,一直流到灵河口,甚至流经以灵河而得名的灵川县境之内,人们则称它为灵河。由此可证,零水就是漓水。
再有,《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地部三十引《临桂图经》说:“漓水出(兴安)县南二十里柘山之阴,西北流至县西南合零渠。”这里所谓县西南二十里的柘山,就其方位和道里来看,当在今唐公背岭一带。由此向西南延伸的山脉,则是香炉界、东山等大山。这里所记的道里虽与《大清一统志》所记郁金山不同,其实是山脉有远近之分而已。据此可知,柘山即郁金山,漓水即零水。
前人对这条河流,有时称零水、澪水或灵河,有时又称漓水或离水,这种称呼的转变,或是由于时代不同而各异,或是由于“零”“澪”“灵”“漓”“离”等字,都是同音或近音一字之转。类似的例子,在我国舆地图籍中常常可见,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可知《水经注》湘漓两篇有关源流之文,并没有错。但是,一些著文讨论湘漓源流的作者,往往囿于因袭之见,抓住《水经注》湘漓两篇里没有提到秦代凿渠之事,坚持二水同源于龙母岩、北流90里至兴安城南渼潭、因凿渠而劈湘分流始有漓水的说法。尽管漓水篇里说在始安峤南有一条自然河流,并清楚写着“(始安)峤水自峤之阳南流注漓”“漓水又南流与沩水合”,有些研究者却对此忽略了,把“水出西北邵陵县(郡)界而东南流注入漓水”的沩水当作漓水之源,从而得出漓水发源于猫儿山的结论。
- 第 1 版: 要闻 孙大伟在南宁防城港钦州崇左市调研时强调 在服务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 第 2 版: 要闻 用文明之花扮靓寿乡——巴马瑶族自治县政协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侧记
- 第 3 版: 要闻 古漓水考辩
- 第 4 版: 要闻 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