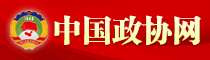郝兴燕
老屋真的要拆了。消息是堂兄在电话里说的,声音隔着千山万水,却像一块巨石砸进我的心底。我推开窗,城市夜晚的灯火明明灭灭,忽然就闻到了老屋天井里那棵栀子花的香气——那香气穿过二十年光阴,依然清冽如初。
老屋的门槛被岁月磨得低矮了。小时候,我总要踮起脚才能跨过去。门槛正中有一道月牙儿般的凹痕,是祖父的藤椅年复一年在这儿摇晃出来的。每年腊月,祖母都要给门槛刷一遍桐油,那味道要在院子里飘上好几天。最后一次见祖母刷桐油,是她去世前那个冬天,她刷得极慢,刷完坐在门槛上喘气,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
天井里的青苔更厚了。雨水顺着黑瓦滴下,在青石板上凿出一个个小坑。靠东墙的那口大水缸还在,缸壁爬满绿茸茸的苔藓。我伸手搅了搅,惊起几只孑孓。七岁那年,我趴在缸边看金鱼,一不小心栽了进去。祖父一把将我捞起,他的手掌粗糙如砂纸,擦得我脸颊生疼。如今水缸里的倒影晃晃悠悠,再也拼凑不出当年的模样。
灶间的土灶已经塌了一半,露出里面的黄泥坯。灶台上供着的灶王爷画像褪了色,但那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祖母总在腊月二十三这天,用麦芽糖粘住灶王爷的嘴,说是让他“上天言好事”。那糖的甜香,至今还在记忆里打着转儿。墙角堆着几捆松枝,是祖母生前捡来烧火的,现在已经朽成了灰褐色,轻轻一碰就碎了。
阁楼的木梯吱呀作响,像在诉说陈年旧事。我的小书桌还在窗前,桌面裂了缝,钻出一簇白茸茸的菌类。翻开抽屉,里面竟还留着半本《新华字典》,书页被蠹虫蛀成了蛛网。字典里夹着一片枫叶书签,叶脉还清晰可辨,只是轻轻一碰就化成了粉末。
堂屋的正梁上,燕子窝空空如也。记得每年春天,燕子都会准时回来,在梁间呢喃细语。祖母不许我们惊扰它们,说燕子认得老家。如今梁上结满蛛网,那只去年的泥窝裂了道缝,像在等待永远不再归来的故人。
我在老屋的废墟间坐了很久。夕阳西下时,堂兄来催我离开。起身的瞬间,衣角勾住了一块松动的墙皮,泥土簌簌落下,露出里面藏着的什么东西——是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
打开盒子,里面是祖父的烟斗,祖母的顶针,我掉的第一颗乳牙,还有一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上的祖父抱着年幼的我,祖母站在身后笑着。
我把铁皮盒子揣进怀里,最后看了一眼老屋。残垣断壁在暮色中像一幅水墨画,而那些远去的光阴,都凝固成了画中永恒的留白。
我想,老屋从不曾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我们的记忆里继续活着——就像梁上的燕子窝,等待每一个懂得怀念的人,在心里为它衔泥筑巢。
- 第 1 版: 要闻 中央宣讲团来桂宣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丁国文作宣讲报告 陈刚主持 韦韬孙大伟出席
- 第 2 版: 精选 成年人“儿童化”是精神返祖吗
- 第 3 版: 关注 买全球惠全球,“出口中国”展现中国市场“磁吸力”
- 第 4 版: 导读 古诗词里的家乡——宜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