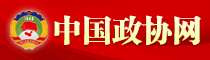王玉美
冬至过后,阳光总来得迟些。午后的风裹着寒气,刮得窗玻璃发颤,我却偏要推开半扇窗——就着这冷意煮茶读书,才是冬天该有的暖。书桌靠窗摆着,上面放着那只粗陶茶壶,是去年在古镇淘来的,壶身上刻着淡淡的梅枝,此刻正安安静静地等着被注满热水,旁边摊开的书,还夹着上周落下的茶渍,像给文字缀了颗小星子。
煮的是去年存的老白茶,茶叶蜷着身子,裹着层淡淡的白霜,像极了冬日枝头未化的雪。水是刚接的井水,带着点凉意,倒进壶里时,“哗啦”一声,惊得窗台上的吊兰晃了晃叶子。我没开电煮茶器,偏用了只小小的银壶,架在迷你炭炉上——总觉得炭火煮的茶,比电煮的多了点烟火气,就像纸质书比电子书多了点墨香。炭是无烟的枣木炭,点着时没什么火苗,只慢慢透着暖意,把银壶底烘得微微发烫,壶里的水也跟着慢慢醒过来,起初是细弱的“滋滋”声,后来便“咕嘟咕嘟”地冒起小泡,像是在跟书页里的文字打招呼。
等水开的间隙,我随手翻了翻桌上的书,是汪曾祺的《人间草木》。书页已经被我翻得有些软,某一页上还夹着片干枯的茉莉花,是夏天泡茶时不小心掉进去的,如今还留着点淡淡的香。翻到写冬天的段落,“天冷了,堂屋里上了槅子。槅子,是春暖时卸下来的,一直在厢屋里放着。现在,搬出来,刷洗干净了,换了新的粉连纸,雪白的纸。上了槅子,显得严紧,安适,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读着读着,竟觉得炭火的暖意又浓了几分,连窗外的寒风都好像温柔了些。
水开了,我提起银壶,把热水缓缓倒进装着白茶的盖碗里。茶叶遇水,慢慢舒展着身子,像刚睡醒的娃娃,在热水里轻轻打了个转,然后便沉到碗底,只把茶汤染成淡淡的琥珀色。第一泡的茶我没喝,只用来温了温杯子——老辈人说,冬日喝茶要“温杯烫盏”,这样喝进嘴里的茶才够暖。第二泡的茶汤倒出来时,香气一下子漫开来,是淡淡的枣香混着药香,钻进鼻腔时,连带着心里的冷意都散了。我捧着温好的杯子,抿了一口茶,茶汤滑过喉咙时,暖得人忍不住喟叹一声,再低头看书里写的“昆明的冬天不冷,我经常在外面散步”,竟觉得自己也跟着汪曾祺先生,走在了昆明暖融融的冬日街头。
以前冬天总爱喝红茶,觉得红茶够浓够暖,后来喝了老白茶,才发现这种不疾不徐的暖,更适合配书读。就像去年冬天,我读《红楼梦》,读到“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那回,窗外正好下着雪,我煮了壶老白茶,就着茶香往下读,看宝玉披着大红猩猩毡斗篷,带着众人在芦雪庵赏雪联诗,竟觉得自己也置身其中,手里的茶杯都像是成了庵里的茶盏,连茶汤都多了几分雅意。还有次读李清照的词,“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心里正觉得怅然,喝了口温热的老白茶,那股暖意从胃里慢慢漫上来,竟把词里的寒凉都中和了些——原来茶与书,竟能这样相互慰藉。
炭炉里的炭还在慢慢燃着,银壶里的水也还冒着热气。我又续了第三泡的茶,茶汤比之前淡了些,却多了几分清甜。书也读到了写水仙的段落,“养水仙,得天天换水。不换水,水就臭了。水仙根里的黏液很多,要常洗。洗的时候,用手指顺着根须捋,黏液就掉了”,读着这些细碎的文字,再看看手里的茶杯,忽然觉得,冬日的暖,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这样细碎的——是炭火的暖意,是茶汤的香甜,是书页里的文字,是窗台上吊兰的轻晃,这些细碎的暖,凑在一起,就把整个冬天都焐热了。
窗外的太阳渐渐西斜,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书页上,像给文字盖了个温柔的章。我合上书,把最后一口茶喝进嘴里,茶的暖意还在,书的墨香也还在。炭炉里的炭已经快燃尽了,只留着点余温,银壶里的水也凉了些,可我却觉得浑身都暖融融的——原来冬日里最实在的暖,从不是靠厚棉衣或暖空调,而是一壶热茶,一本好书,还有一颗愿意慢下来的心。
收拾茶杯时,我把那片干枯的茉莉花重新夹回书里,又给窗台上的吊兰浇了点水。风还在窗外刮着,可我心里却像揣了个小炭炉,满是暖意。我想,下次再读这本书时,闻到的定不只是墨香,还有今日的茶香,和冬日里那点细碎的、安稳的暖。
- 第 1 版: 要闻 中国高水平开放新答卷——从海南自贸港封关看中国制度型开放
- 第 2 版: 生活经纬 低GI食品受追捧,是生活新选还是消费陷阱?
- 第 3 版: 社会 “看不懂”的景区标识——多地知名景区翻译乱象调查
- 第 4 版: 周末闲情 最短昼 最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