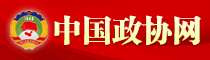王 晗
我回村的时候,日头刚偏西,风把稻浪推得一层又一层。路旁狗尾草半人高,穗子轻轻扫过裤脚,留下淡淡的青痕,像顽皮孩子用毛笔蘸了清水,在布料上试笔。
我放慢脚步,低头看落叶。杨树叶阔,边缘卷成汤匙,盛着一点碎金般的日影;槐树叶小,却多,叠在一起像旧信笺,纸色被雨水和尘土反复晕染。一脚踩下,叶梗折断,脆生生的触感从鞋底传到膝盖。古人说“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其实不必慨然,这声音只是提醒我:慢些,再慢些。
小径拐过池塘,水面上浮着一层薄暮,像谁遗落的纱巾。纱巾下,菱角叶团团簇拥,叶背泛着暗红,像村妇悄悄擦了胭脂。塘边芦苇弯腰,穗头轻点水面,留下一圈极细的涟漪,转眼就被风抹平。我想起小时候,祖母把嫩菱角煮在饭锅里,开锅时蒸汽带着微甜的腥香,锅盖一掀,白米上躺着乌亮的菱角米,像一颗颗小马蹄。如今祖母的灶台冷了下来,池塘却还在,一年一年地长新菱,替旧人守着旧味。
再往前,是一块收了豆子的空地。豆茬短而硬,像无数支倒插的小箭,鞋底踏上去,先是一顿,再微微陷下,箭杆折断处渗出青涩的汁水。空地上晒着红辣椒,一串串挂在枯枝搭成的架子上,远远看去像一簇簇小火苗,把黄昏烧得更暖。我伸手捏了捏,椒皮皱而脆,指腹沾了一点辛辣,凑到鼻前,眼泪差点被呛出来。这味道直通胸腔,像把胸腔里积了一夏的闷热猛地撕开一道口子。
田埂上,野菊花开得正碎,黄的白的小纽扣一样,撒在杂草间。我蹲下来,指尖碰了碰花瓣,薄得像浸湿的棉纸,凉意顺着指尖爬上来。小时候,母亲把这种小花叫“油菊”,采回一篮,铺在竹匾里晾干,冬天泡进热水,给放学回来的我洗脚。那香气极淡,却能在湿冷的被窝里停留一整夜。如今我已多年没泡过那样的脚,可每次看见野菊,脚背就隐隐发热,仿佛水盆还搁在堂屋中央,水纹里浮着几粒花骨朵。
日头更低,小径被拉长的影子切成一段明一段暗。我踩进暗处,凉意从脚踝往上爬,像井水漫过桶沿。抬头望,天空被晚霞烘出层次:近处是淡绯,像新嫁娘的腮;远处是灰紫,像旧年棉袄洗得发白的里子。风掠过树梢,树枝轻轻摇晃,落下最后几片叶子,它们在空中打着旋,像迟迟不肯落地的信笺。我忽然明白,所谓“秋纱”,不过是光线、落叶、草屑、尘土混在一起,织成的一张薄网,人走在里头,每一步都把它撞得微微颤动,像用手指轻弹一匹极软的绸。
走到村口老槐树下,天已擦黑。树影浓得像墨,把小路尽头吞进去。我回头望,来时的脚印深深浅浅,印在碎叶与尘土上,像一串省略号,留给后面的夜读。树洞里蹲着一只猫,黄眼睛在暗处亮了一下,又隐去。我摸摸口袋,还有半块早晨买的芝麻饼,掰开放在树根下。饼屑落在落叶上,分不清哪是饼渣,哪是叶脉。
我踏进门槛,母亲正从灶间出来,手里端着一碗新蒸的芋头。热气在她指缝里缠绕,像不肯散去的白纱。我伸手接过,指尖被烫得微微发麻。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已把整条小径、整幅秋纱,都收进了掌心。
- 第 1 版: 要闻 为“折翼的天使”再造翅膀——广西首家工疗型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见闻
- 第 2 版: 精选 保健品“营养指导”靠谱吗
- 第 3 版: 关注 垃圾成堆、钟乳石被售卖——天然溶洞遭破坏调查
- 第 4 版: 导读 小鼎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