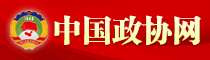郝兴燕
院角的石榴树又开花了。那红,不是明艳的朱砂红,倒像是谁家姑娘的胭脂晕染开来,又掺了些许夕阳的余烬。我站在树下,看那花瓣一片片跌落,忽然想起幼时祖母用石榴皮染布的事来。
祖母是个极会过日子的。秋深了,石榴熟透,她总要留下那些剥下的石榴皮,晒在竹匾里。那些干枯的皮,蜷曲如老人的手指,却藏着惊人的颜色。待得冬日,她便取出来,与白布同煮。不多时,那清水便成了琥珀色,布料渐渐染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黄——不是明黄,也不是土黄,倒像是秋叶将落未落时的颜色。我常蹲在灶边看,看那颜色如何一点一点渗进布里,如同岁月如何一点一点渗进人的肌肤。
而今想来,那石榴皮染就的,何尝不是光阴的颜色?
邻家王婆的院子里有一株老梅,据说比我父亲的年岁还要长。每年腊月,那梅树便开出细碎的白花,香气清冷,却能飘过两重院落,直钻进我的窗棂。王婆是个孤老,却极爱那株梅树。我常见她立在树下,用那双布满老人斑的手,轻轻抚过粗糙的树皮,如同抚慰一个老友。去年冬天,王婆走了,那株梅树却依然开花,只是再无人立在树下,仰头细数那些花朵了。
草木的生命,原比人长久得多。
巷口卖豆腐的老张,每日清晨必在担子上插几枝新鲜的栀子。那花儿雪白,衬着青翠的叶子,在晨光里格外精神。老张说,这是他家院子里长的,不费什么事,却能让人看了欢喜。的确,买豆腐的人见了那花儿,总要夸赞几句,老张便笑得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后来老张的豆腐摊没了,那带着栀子花香的清晨,也再寻不见了。
前日路过旧巷,竟在瓦砾堆中看见一株栀子,不知是不是老张家那株的后代。它从砖缝里挣出来,开着两三朵花,虽不及老张担子上那些饱满,却也洁白如初。我蹲下身,嗅了嗅,香气依旧。
最是寻常草木,偏能系住最深的乡愁。
楼下的小菜园里,李婶年年种丝瓜。那藤蔓爬上竹架,开出黄花,结出青果,到了夏末,便垂下一根根老丝瓜。李婶总要留几根在架上,任它们枯黄,最后只剩下纤维的筋骨。她用这丝瓜络洗碗,说比城里买的什么海绵都好用。我笑她节俭,她却说:“这不是节俭,是念旧。”原来这丝瓜种子,是她从老家带来的,已经种了二十多年。
今年春天,李婶回了乡下,那方小菜园便荒了。前几日经过,竟看见几株丝瓜苗从杂草中钻出来,也不知是去年落下的种子,还是风从别处吹来的。它们攀着残存的竹架,努力向上生长。我想,到了秋天,或许又能看见几根老丝瓜在风里摇晃吧。
这些草木,它们不言不语,却记住了我们所有的故事。石榴记得祖母染布的手,梅树记得王婆仰望的目光,栀子记得老张担子上的晨露,丝瓜记得李婶年复一年的期盼。而我们这些所谓有灵性的人,反倒常常忘记。
夜深了,我站在窗前,忽然嗅到一阵若有若无的花香。这城市里,不知是哪一株草木,又在静默地记取着谁的故事。或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去,而这些草木依然会在原地,开着花,结着果,将我们的故事,讲给风听。
- 第 1 版: 要闻 广西出台措施撬动各类资本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 第 2 版: 精选 打造县域经济强力“引擎”——隆安县政协助推工业强基攻坚行动取得新突破
- 第 3 版: 关注 以调查研究之钥 当好实体经济服务员
- 第 4 版: 导读 蝉声未远,雁已衔秋来